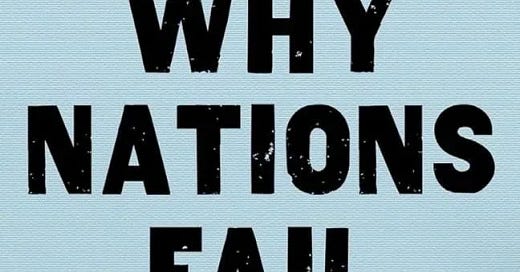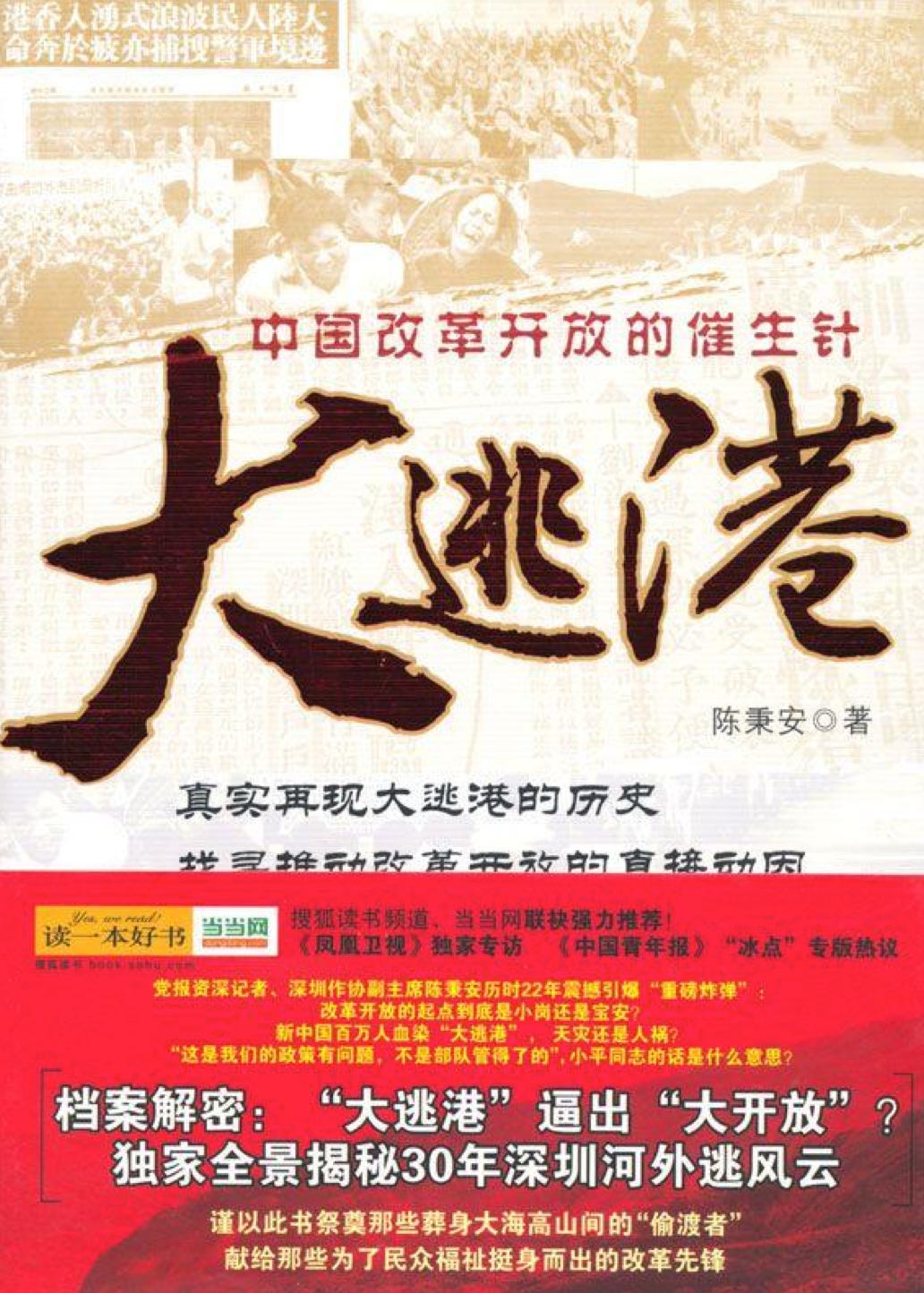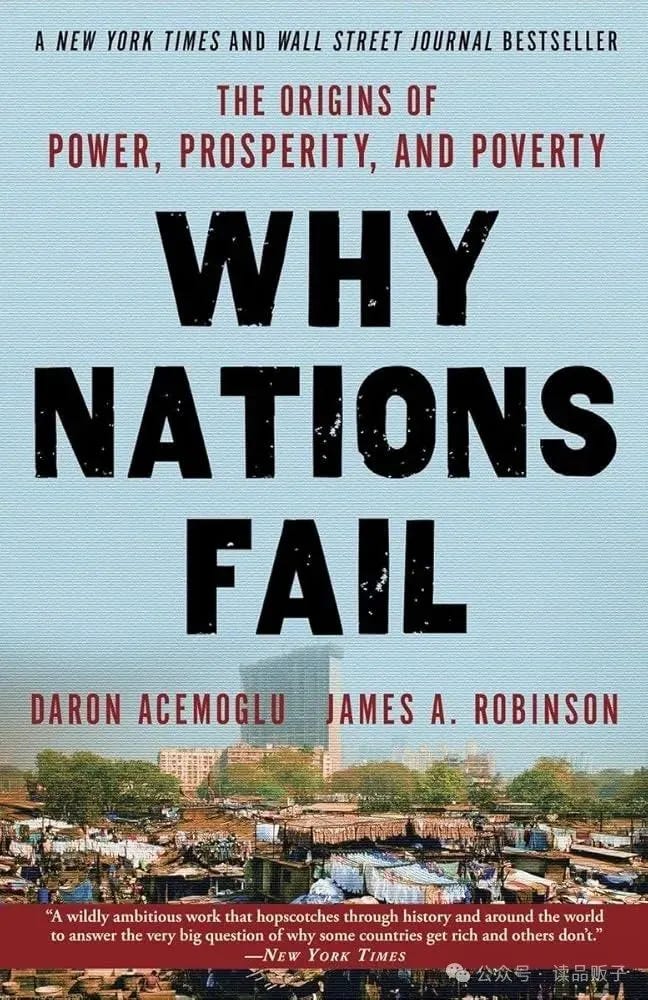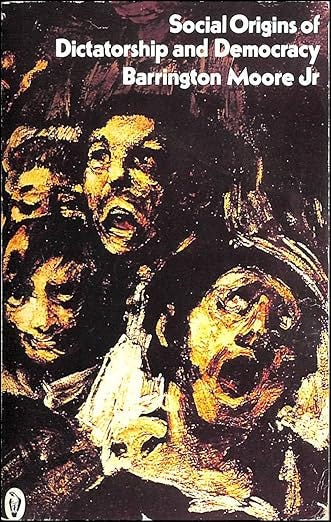国家兴与否,制度主沉浮: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简评
李华芳 | 匹兹堡大学
2024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简介之一之前发过一遍,主要是评价Why Nations Fail那本书的,参见《兴于包容、毁于榨取》。这里重新写一篇,最后加入了几句我对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关系的理解。
1,
所有有雄心的经济学家的工作都或多或少试图回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典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几百年来,学者讨论了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劳动力、投资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但没有正式解决一个遗留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在两个差不多的地方,资源禀赋相差无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也近乎一样,为什么还是有发展的差异?
一种解释是劳动力虽然投入看起来差不多,比如你都雇佣了100个人,但这100人是大学生还是初中生,是有本质区别的。就算表面上人数一样,但人力资本是完全不同的。而教育和培训一直都是增强人力资本的有效方式。所以有不少学者跟进人力资本和教育培训的研究。
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是靠这些要素决定,那么长此以往后发国家不是能够学到先进国家的经验,然后赶上来吗?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能看到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慢慢趋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漫长的历史中观察到这种经济发展趋同的情况,反而是贫富差距拉大倒是常态。
根据诺思、张五常等人发现,就算是两个地方都靠近港口、气候宜人、工人素质相近数量也差不多、然后你再投入差不多的资金,发展依旧会有很大的差异,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制度不同。
同样的要素,不同的制度安排,就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经济结果。正如周其仁经常说的,在东北大冷天里农民在公家的地里枕着锄头睡觉,回到自家的自留地里就拼命干活,人、地、投入都差不多,但公地和自留地的产权制度不同,人的积极性就不同,经济产出也大不一样。
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这才是一个国家兴衰与否的原因。这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坊间常用他们姓氏的首字母AJR来称呼这三人)的贡献。他们以极具雄心的写作回应了经济学的经典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
2,
AJR的答案是“制度”。正如前面提到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并不是AJR的首创。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的贡献也是制度经济学,关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
AJR的贡献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确认了不同的制度,尤其是划分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和不利于增长的“榨取性制度(exclusive institution)”。在AJR2001年AER的文章《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里,他们提出了榨取性制度这个概念,主要是指生活在这种制度下的大多数人都缺乏法治和产权保护,并且当政治权力掌握在极少数精英手中时,更有可能实施榨取性制度。尽管精英与大众的博弈更复杂一些,这个稍后会提及。
而在AJR在2005年写了一章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收录在 Aghion和Durlauf主编的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里。在这一章里,他们定义了所谓好的经济制度,是指那些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强有力执行产权的制度。好的经济制度确立清晰产权解决激励问题,并且市场允许自由进出,政治治理上也体现为尊重大部分的利益,并且能够有效限制独裁,约束精英的榨取行为。至于产权为什么重要,那就是从科斯到周其仁的传统了。周其仁等还强调了法治,哪怕是不完善的法治,也对市场运行有重要的作用。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2012的书《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里,把这一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统称为“包容性制度”。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述截然相反,AJR的中心论点是良好的政治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是上层建筑影响了经济繁荣。
也就是通过他们的研究,我们对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增长,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经济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通过长期研究,大致确认有一些制度安排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这个在“华盛顿共识”中得到了统一的体现,简单总结起来大概就是“个人有自由,市场起作用,法治得保障”,这样经济就能发展起来。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更容易采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
AJR第二方面的贡献是通过一系列因果识别的办法,确认包容性制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制度影响经济,听起来并不复杂。但要从因果关系上确认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AJR的系列研究给我们展示了确认制度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办法。
3,
在进入正题之前,让我先来讲一个大逃港的故事,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什么又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榨取性制度。1950年代后期的深圳与香港,一河之隔,但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百倍之差。这导致从50年代一直到改革开放,按照陈秉安在《大逃港》里的测算,至少超过百万人用各种办法从内地来到了香港,而游泳过河是最常见的手段。
我觉得最令人动容的例子是香港新界的罗芳村。香港新界本来是没有这个罗芳村。深圳宝安县倒是有一个罗芳村。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在年终汇报里说,罗芳村只剩一个人,是个瘸子,而其他人都逃到香港去了。所以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其实就是深圳的整个罗芳村村民过去之后新建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深圳罗芳村人要整个村都逃到香港去呢?明明一河之隔,按理说地理气候资源甚至人都差不多,为什么要费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到香港去?
答案也不复杂,那就是去香港有希望,能找生活,活得下去还能有发展。而造成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如此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个地方实行不同的制度。
大逃港最终导致深圳设立特区,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无非就是要学一点香港的制度,把经济搞上去。至于香港回归至今,到底是不是马照跑舞照跳,维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呢?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没有趋近呢?可能大家都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可以想想看背后的原因。
4,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Why Nations Fail》一书里用了另一个例子,那就是诺嘉乐(Nogales)地区。我之前写过《兴于包容,毁于榨取》,里面也提到过惯常讨论过的地理、文化和领袖,或许可以解释部分各国发展的差异。但问题也恰在于这三个因素无法全然回答在南北诺嘉乐(Nogales)地区的差异。诺嘉乐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的当然是亚利桑那州(Arizona)以及美国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属于索诺拉(Sonora)州,却是墨西哥的领地,实行墨西哥制度。
两个地方南北接壤,地理位置没什么不同,文化差异也不大,都是那一群人,鉴于每年大量墨西哥移民到美国的事实,似乎也表明墨西哥人也知道怎么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很难想象墨西哥的领导人会不清楚那些普适的经济发展原则。所以地理、文化和领袖这几个因素都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南北诺嘉乐会呈现出如此不同的面貌。也因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之前的理论需要修正。
两人发现南北诺嘉乐地区最不相同的是“制度”。美式民主宪政制度在经济上保护私人产权、实施法治、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且市场运行得到国家支持、市场向新的企业开放、市场上的个体遵守契约、并且人们可以获得教育和普遍的致富机会。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在政治上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允许广泛的公民及其团体的政治参与、对政治家有制度性的问责和约束、依法行政、而联邦政府有一定的集权来有效实施法律。这种制度被作者称为“包容性制度”,与此相对的是“榨取性制度”。此处我译成榨取性制度,并没有直接对应exclusive“排外的、排斥的”的意思,因为榨取性制度,更能体现统治者不仅不愿意与大众分享经济成果,而且会采用政治制度来榨取大众,与民争利的行为。
5,
当然AJR不研究香港的殖民史和发展史,但香港其实也是AJR2001年AER的文章以及2002年QJE文章《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的一个现实脚注。在这两篇开创性的论文,AJR奠定了一个研究制度对长期经济影响的框架,并且提供了殖民对长期繁荣影响的证据。简单来说就是,殖民者选择何种制度,会影响殖民地的长期繁荣。
但影响长期繁荣的因素太多了,比如1974年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各自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认为地理、气候或疾病负担相关的因素决定了国富国穷。但哈耶克则认为法律重要,并且为什么国家间发展有差异是因为采用法律体系不同,比如英国普通法要好过法国民法。这一点在1998年被LLSV(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 Vishny)的文章《Law and Finance》证实。
要确定制度并且只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要剥离其他因素(地理气候文化等)的影响,并且处理制度的内生性问题。所谓制度的内生性,在这里是指制度往往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而被刻意选择的,例如深圳特区。
AJR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中迎难而上。这两篇文章利用欧洲殖民者在其殖民地国家采用的不同制度,巧妙研究了制度对长期繁荣的影响。假定殖民者选择一种制度是为了利益最大化,那么殖民者在殖民地就会权衡成本和收益,而成本和收益受到殖民地初始条件的影响。
那么初始条件有哪些呢?AJR认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初始条件是人口规模。如果一个地方人比较多,那殖民者进入的时候遭遇反抗的概率就比较大,发生冲突几率大意味着定居者死亡率就比较高;但与此同时,人多意味着在殖民者进入前的初始条件还不错,可能往来贸易多,经济发展还可以,这就意味着资源多,殖民者可以抢夺的东西就多,比如黄金白银糖香料等。反之,如果地广人稀,那殖民者不容易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更容易定居下来。
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所谓“财富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的推论。也就是说,如果殖民制度对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话,那么殖民时期繁荣的国家今天应该更加贫困,因为高死亡率迫使欧洲殖民者采用短期榨取各种资源的策略,不太会考虑建设保护产权的包容性制度。但是如果殖民时期比较贫困的国家,殖民者能轻松定居,就更容易引入包容性制度,从长远来看反而助益了经济繁荣。
这是不是与事实相符呢?在AJR2002年的文章中,他们通过研究20世纪末人均GDP与大约1500年时的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之间的关系,确实发现了财富逆转与数据相符,1500年时相对富裕的国家如今相对贫穷。换句话说,在殖民统治之前较为繁荣的地区现在相对不那么繁荣了。因为财富逆转并不是1500年之后全世界的普遍现象,这种逆转也没有发生在未被殖民的国家中,并且在欧洲殖民活动出现前500年里也没有逆转,所以AJR的文章实际上是暗示了这一切与欧洲殖民有关。
6,
但是正如之前所言,制度是内生的。怎么样从众多影响因素中分离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因果性影响呢?AJR这里使用了一个制度的工具变量,那就是殖民地死亡率。
AJR等意识到疾病是一个地方重要的初始条件。例如在热带地区,由于疟疾和黄热病等疾病肆虐,定居者死亡率就很高。欧洲人如果去这些地方殖民定居,就不容易,因为很容易生病死掉。所以欧洲殖民者一旦发现这些地方,就容易采用短平快策略榨取当地资源,不太会放眼长远,建设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包容性制度。
相反,如果是在温带地区,比如说加拿大和美国,由于没有类似疟疾和黄热病等困扰,定居者死亡率比较低,欧洲殖民者大量进入之后,就回建立包容性制度。因为他们会想着在这些地方扎下根来,作长远打算,而不是快进快出榨取完了事。
所以AJR2001年的文章就假定欧洲殖民者倾向于在死亡率相对较低的地方定居。而定居者带来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并发展出类似家乡的制度,尤其是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在因疟疾和黄热病等疾病导致死亡率较高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并没有大量定居,而是建立或维持旨在尽可能多、尽快地从土著居民那里攫取资源的制度。所以可以用殖民地定居者死亡率来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死亡率高则采用榨取性制度,而死亡率低就建立包容性制度。而殖民国家和制度的许多特征在那些国家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后依然存在,并且持续影响这些国家当下的经济繁荣。
正如AJR在2001年的文章中展示的,定居者死亡率与当代经济繁荣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意思是定居者死亡率高的地方现在的经济情况比较糟糕。换句话说,采用榨取性制度的殖民地国家,哪怕后来独立了,也是经济发展不太行,人民比较穷。其推论就是包容性制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7,
AJR2001年的文章当然也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我们先不说殖民地制度到底有多重要,因为这个极端依赖于“定居者死亡率”这个工具变量,并且这个工具变量依赖于极强的假设,也就是“定居者死亡率”只能通过影响“制度”进而影响经济繁荣,而没有其他影响路径。
一个重要的反对意见是Albouy2012年对18世纪定居者死亡率数据可靠性的质疑。当然AJR的回应没有那么强硬,可能因为这个属于硬伤。他们只是说,在排除那些Albouy指出的有争议的非洲国家后,他们2001文章的核心结果仍然是成立。所以让学者认错真的很难。但这篇文章有个意外的后果,就是吸引了一大批历史学家加入到批评经济学家的阵营里。历史学家大抵觉得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原来经济学家这么不可靠,基本史实出错的比比皆是。当然也有不少相互合作的,希望不久的将来,跨学科合作能产生更多的佳作,当然这只是我的希望而已。
在诸多反对意见中,Glaeser等人2004年在《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一文中的反驳在我看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顺便说一句,Glaeser的合作者就是前面提到著名的LLSV中的LLS。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针对“没有其他影响路径”这一说法的。定居者不仅影响制度,也带来了知识,那么怎么处理定居者带动人力资本积累而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路径呢?换句话说,定居者死亡率不仅仅影响制度,也影响人力资本,而我们知道哪怕是榨取性制度下,受教育人数增加也能推动经济发展。而AJR的死亡工具变量不能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我们考虑AJR研究的财富逆转现象,若非殖民者采用榨取性制度,就不容易解释为什么曾经繁荣的地区变得不再繁荣。但这些辩护多少也比较无力,还不如直接说“没有完美的工具变量”来得坦荡些。
8,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包容性制度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后发国家也可以学习,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国家都采用包容性制度,然后大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呢?比如说为什么南北韩的制度过了这么久还不趋同呢?AJR的答案是要从统治者身上找原因。
为什么统治精英会采用榨取性制度或者包容性制度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路延展开来的理论就认为随着人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例如中产阶级规模变大,他们迟早会有政治上的诉求,所以寻求政治参与最终导致制度变革,所谓经济发展带来民主。
另外一路理论主要关心精英之间的博弈互动,而民主不过是这个过程带来的副产品。反正几大家族谁也打败不了谁,不如设计一个民主规则,大家风水轮流转,一起统治老百姓来获取利益。当然这一路的问题也是总有有野心的精英试图打破这个规则,一家独大,所以充满了不确定性。
上面这两路理论第一路是自下而上,第二路是自上而下,取决于观察的对象不同。略有不同的是第三种社会运动的视角。我觉得摩尔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s and Democracy: Lor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一书中的观点深得我心,当然这也取决于我自己的观察对象。这一路的重点的社会动员,被压迫的人民如果能动员起来,就能推翻精英的统治。也非常符合中国革命的叙事逻辑。
第三路视角遇到的挑战是如果统治精英非常自信,觉得有能力控制社会,他们就不怕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因为他们认定群众的威胁不可置信,因而不会愿意实行放权的改革,更不可能与反对派进行所谓民主化的谈判。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系列作品,其实就是对韩国民主化过程的文学记录。尤其是在《少年行》中,各个不同群众的视角展示了精英不愿意谈判但群众尽管集体行动困难却没有放弃的艰辛历程。
AJR在这里的贡献是模型化了社会冲突、精英统治所遭遇的周期性威胁、以及可置信承诺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新,但AJR的贡献是建立一个统一跨时期的分析框架,将不同视角置于一个模型里。
9,
在AJR的基础模型中,精英掌权,国家在预算平衡约束下运作,也就是说税收和转移支付相等。但因为精英掌权,在两部门经济中,他们就可以隐藏全部收入。而群众只能隐藏在非正式部门的收入,从正式部门获得的收入必须交税。如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消费,那么在基本模型设定中,每个人剩下用于消费的是税后收入和获得的转移支付,当然也要减去资源转移给他人的部分例如捐赠之类的。
这样税收实际上变成了精英统治大众的工具,体现为多种形式,例如征用土地和资产、设置准入(例如需要各种资质证件等才能从事经济活动)、以及操纵价格等。反正在这种设定中,税收的实质是将群众的利益转移给精英。
但也不能认为群众都是群氓。群众也有最后一招,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0年QJE的文章《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群众有能力推翻精英统治。但是革命是有成本的,他们用参数 𝜇 ∈ (0,1) 来代表群众的“革命成本”:𝜇 越低,发动革命的成本越高。
如果没有民主,精英掌权,精英在群众做出投资和消费决策后,就会尽可能多的从群众那里攫取资源。但群众会预测到精英的这个决策,所以会将他们的资产投入非正式部门,因为在那里他们能隐藏部分资产。简化模型情况,就是群众预测到精英要来剥削了,就把所有资产转移到非正式部门隐藏起来,精英就无法通过征税从群众那里获得收益。而在民主情况下,简化为群众掌握权力的情况,那么群众就会设定税率为0,所有人都会将资产投到正式部门,因为收益高但税率为0。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模型可以推导出革命约束条件,就是推断群众何时会革命。存在一个 𝜇∗ ∈ (0,1),使得革命约束成立。如果 𝜇 > 𝜇∗,群众将发动革命;精英不放权的话就会导致革命,并且精英无法征用群众的资产,长期来看经济上也难以为继。那么精英会放权,例如给群众选票。反之,如果 𝜇 ≤ 𝜇∗,则群众的革命威胁就不可置信,因为群众不会发动革命,精英就会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并设定最大税率为1,最大程度攫取群众利益。
10,
上述是基于承诺不可置信的情况,因为精英和群众之间不可谈判。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进一步放宽假设,允许精英和群众谈判,谈判中承诺可置信。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可以和精英谈判,决定是否发动革命,以及在每种情况下的税收和转移支付及私人转移支付包括捐赠等都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双方达成谈判解决方案,他们会对此做出承诺,并后续执行该解决方案。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就回到之前讨论的没有承诺的情形中。群众和精英的收益与之前分析的没有承诺情况相同,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可置信的有承诺的协议,群众资产将继续流向非正式部门,精英将设定最大税率攫取尽可能多的资源。
而群众的选择依然受到革命成本的影响。如果大众选择不革命,他们将接受现状,精英则利用这一点继续剥削大众,确保自己能够从经济中获得最大利益。相反,如果大众选择发动革命,尽管面临革命成本,但如果革命的潜在收益足够高,他们可能会尝试推翻精英的统治。但即便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为1,但由于革命会导致经济资产的部分损失,最终的收益仍然会受到影响。因此,革命成本 𝜇 在这里就是一个关键因素,它决定了大众是否有动力去改变现状。
不可置信的承诺为民主化提供了解释。正如分析所示,当 𝜇 > 𝜇* 时,在无法承诺的情况下会发生民主化,扩展选民权利是未来再分配的唯一可靠承诺。但如果没有承诺机制,精英在掌权情况下对未来进行再分配的承诺,根本不可信。而缺乏承诺解释了低效经济制度的持续存在。如果 𝜇 ≤ 𝜇*,则结果是低效的,因为存在帕累托改善,而承诺将消除这种低效。而当承诺成为可能时,低效的经济制度并不要求民主。
由于 𝜇 是动态的,体现了群众在机会窗口中(可不可以搞革命)的想法。群众和精英都知道 𝜇 会以一定概率出现较“高”值,所以每个时期双方都会根据折现的预期未来收益来来行动。如果精英在 𝜇 低的环境中控制政治制度,例如精英可以强势镇压群众,或因为群众一盘散沙组织起集体行动的成本太高,那么税率就会很高,群众在正式部门的投资会很少。而且,即便 在𝜇 较高的环境中,精英仍可能通过实施临时政策调整来维持权力,以防止群众运动。基于这两个原因,低效制度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总之,如果缺乏可置信的有承诺的协议,群众和精英的收益将继续受到制度和政策限制的影响,而未达成协议则意味着缺乏解决冲突的有效手段。精英和群众都面临不确定性,可能不断发生政治动荡,或者得过且过将就下去,直到其中一方不可忍受。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一个洞见是,政治转型(向民主转型)发生的原因在于当前的转移无法保证未来的转移,这一现象归因于承诺问题。而扩展选举权会改变未来的政治均衡,充当持续再分配的承诺。为什么这些社会的统治精英会同意重新分配资源,并放弃对正式政治机构的控制呢?因为这种经济和政治改革可以视为精英为防止社会动荡和革命所做出的战略决策,后者最终会对他们造成更大的损害(比如入狱甚至被砍头)。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不仅形式化了政治精英对广泛社会动荡和革命的战略决策,还帮助解释了不同国家之间制度改革的顺序差异。具体而言,精英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方式应对革命威胁。首先,他们可以扩展选举权,将政治权力交给群众。这一情况在许多北欧、拉丁美洲和(后来的)亚洲国家中发生。其次,精英可以选择保持非民主状态,但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以消除威胁。这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没有扩展选举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建立基础福利国家。
11,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1年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补充性的问题:为什么一些国家未能实现民主的永久转型,而是反复在非民主和民主之间摇摆?
与之前的模型一致,这一次他们考虑了一个包含群众和精英、经济政策以及决定民主或非民主的政治权力集团的模型。在这个扩展版模型里,可能的政治转型范围不仅限于精英扩展选举权以避免群众运动和革命威胁的成本,而是精英还有其他可选择策略,例如发动政变以重新获得对新建立的民主政权的政治控制。
这样在这个扩展的理论框架中,存在多个平衡,而不仅仅是单次转向民主。也就是说,某一平衡可能是不稳定的,即便在某一时期实现了民主,群众在后续时期可能也无法找到防止精英发动政变的政策。
同样,原因在于缺乏对未来政策的承诺。也就是说,群众低水平未来税收以防止政变的承诺在精英看起来不可置信,精英更可能通过政变来重新掌握权力,即使政变对群众和精英来说都是巨大的浪费。
但也有可能出现民主被虏获的均衡。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2008年的论文《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中证明,民主政权持续存在但采取了有利于少数精英群体的经济制度,这种情况也可以是一种均衡。
该模型解释了“被俘获的民主”现象,即少数精英在民主国家控制经济制度。这一回他们用的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的历史实例。尽管美国内战后废除了奴隶制,前奴隶被解放成了自由人,并且获得了选举权。但南方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保留了战前的农业体系,特征为大种植园、低薪无技能劳动力和劳动压迫,这导致南方直到20世纪中期之前相对贫困。南方劳动压迫的延续反映了一种动态过程,其中政治制度的变化被事实政治权力的行使所抵消。也就是说,奴隶制被“单卖主垄断安排、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政治剥夺和恐吓及暴力行为等”一种变相维护南方少数精英的体制所取代。
在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05年致敬摩尔的书《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中,他们细化了之前的模型,与前面的模型假设群众在发起革命时成功的概率始终为1不同,因为革命大部分情况下实际上是未能成功,哪怕同志再努力也不行。说一旦群众决定革命就会成功,这个假设与真实世界那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而且统治精英虽然可以选择镇压群众,但是正如群众面临革命成本 𝜇 表示,精英也面临镇压成本。他们引入了“镇压成本的临界水平”,这与革命约束产生相同的作用。如果放弃政治权力而不进行斗争的收益大于在最优镇压率下的预期收益,精英就不会镇压群众。在这个更丰富的模型中,精英现在有三种选择:民主化、再分配政治和压制。而精英和群众有成本的动态博弈,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即稳定民主、不稳定民主或稳定非民主。
12,
后续大量的工作是围绕“革命威胁”的实证工作,例如Aidt 和 Jensen2014年的文章《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Franchise extensions and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in Europe》,通过记录1820年至1938年间欧洲的42起革命事件,量化了革命威胁的程度。他们认为政权争夺和革命的信息在国际上传播,因此他们估计了这些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滞后对扩展选民权的影响。结果显示这种影响显著且幅度相当大。沿着类似的思路,Aidt 和 Leon2016的文章《The democrat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Evidence from riots in Sub-Saharan Africa》发现干旱模式变化引发的骚乱强度导致了1990年至2007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民主画转型。
另一路是继续深化精英与群众动态无限期博弈中的承诺问题。Powell在2004年的文章《The inefficient use of power: Costly conflict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中,将其总结为由于革命机会波动或增长率变化导致精英和群众相对讨价还价能力的快速变化,可能导致谈判破裂。谈判破裂即使在完全信息的情境下也可能出现,就是因为讨价还价能力的动态变化。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制度即使在长期内也可能效率低下,以及掌权者为何可能积极阻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效率可能(成本收益分析)与精英和群众的目标存在偏差,尤其是缺乏承诺可置信的情况下,冲突往往难以避免。对精英来说,底层制度环境越弱,榨取或者剥削群众的边际收益就越高。但群众也不是吃素的,如果革命的预期收益足够大,总有光脚不怕穿鞋的。
尽管AJR未能解释为何某些国家依然陷入贫困,也未能给出国家何以才能脱离贫困,但他们的研究增进了我们对此的理解。并且AJR还识别了一些关键因素,例如群众与精英掌权的价值、发动和压制革命的成本、缺乏承诺以及革命成功的可能性等,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政治制度的变革和存续。
我认为AJR的研究还缺了一角,那就是在制度没有发生大变化的情况下,改善公共管理,也能极大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打开政府这个黑箱,把公共管理引进来。因为即便是民主制,行之有效和人为扭曲的行政措施,不仅会对群众利益有影响,也会对制度存续有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管理的学者们大有可为。
参考文献:
陈秉安,2010,《大逃港》,广东人民出版社。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00). Why did the West extend the franchise? Democracy,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 1167-1199.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01). A theory of political transi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938-963.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5). Institu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Long-Run Growth, in Aghion, P.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 1A, Amsterdam, NL: Elsevier, North-Holland.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05).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08).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1), 267-293.
Acemoglu, D., & Robinson, J. A.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Business.
Aidt, T. S., & Jensen, P. S. (2014).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Franchise extensions and the threat of revolution in Europe, 1820–1938.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2, 52-75.
Aidt, T. S., & Leon, G. (2016). The democratic window of opportunity: Evidence from riots in Sub-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0(4), 694-717.
Albouy, D. (2012).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2, 3059–3076.
Glaeser, E., R. La Porta, F. Lopez-de-Silanes, and A. Shleifer (2004). Do Institutions Cause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9, 271–303.
La Porta, R., F. Lopez-de-Silanes, A. Shleifer, R. Vishny (1998).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1113-1155.
Moore, B.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s and Democracy: Lor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Powell, R. (2004). The inefficient use of power: Costly conflict with complete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2), 231-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