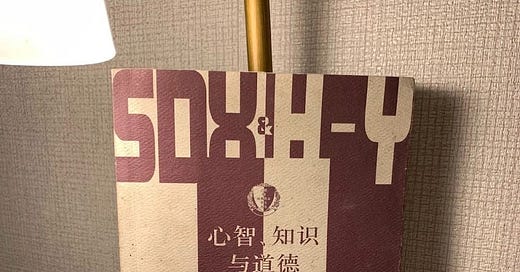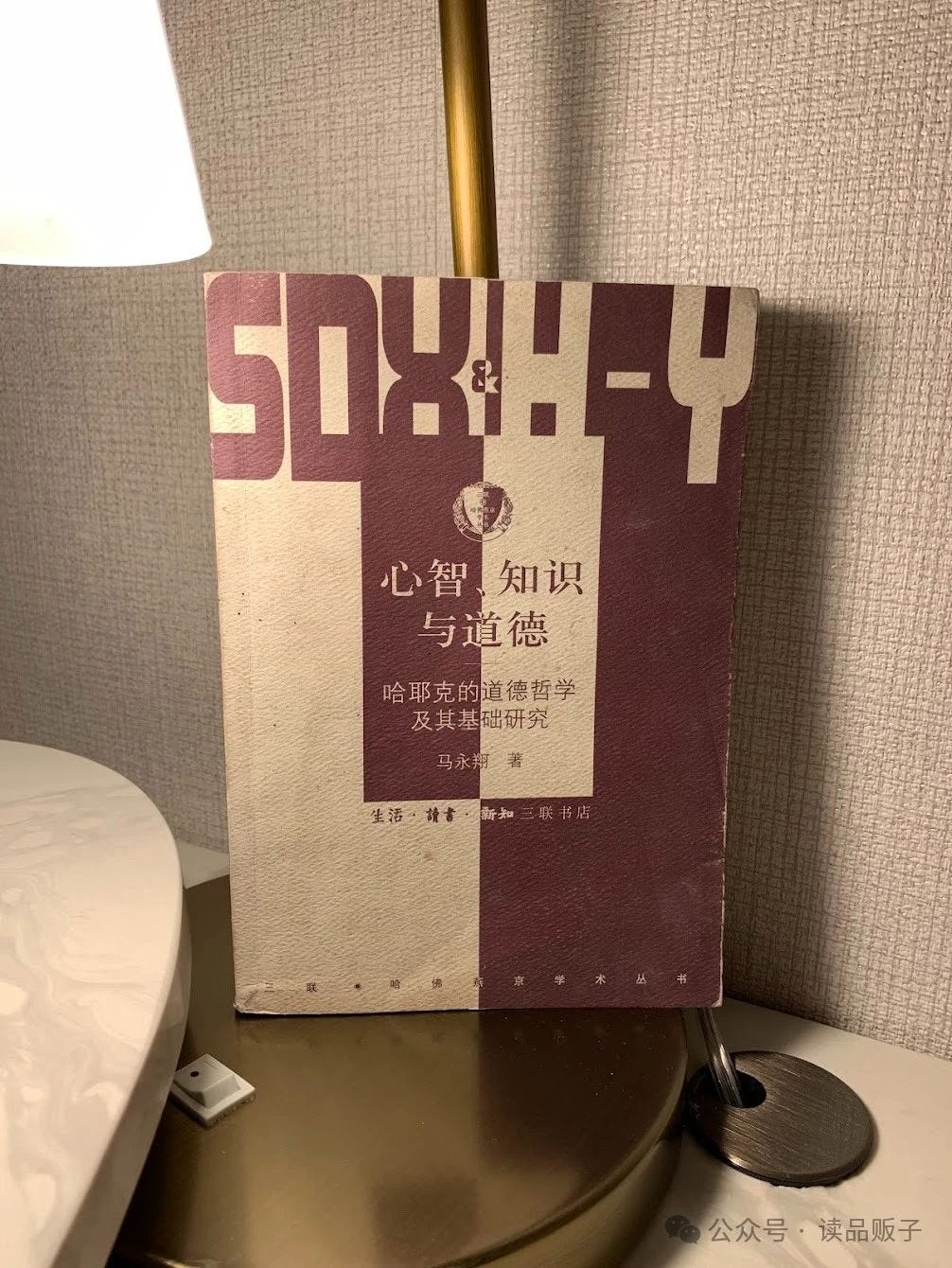2024ARNOVA参会杂记:中国问题,还是以中国解理论问题
2024ARNOVA参会杂记:中国问题,还是以中国解理论问题
李华芳 | 匹兹堡大学
1,
2024年的ARNOVA年会在华盛顿DC开,有回家的感觉,尤其是从机场掏出多年前的地铁卡,发现里面还有钱还能用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之前在DC的America University读硕士,然后在K街附近的智库实习。在美国这多年,转过不少城市,我还挺喜欢DC的建筑,气候,和说不上来的氛围。所以尽管飞机从匹兹堡晚点起飞,也不影响我的心情。
托中盛从国内带了一本马永翔老师的书《心智、知识与道德:哈耶克的道德哲学及其基础研究》过来。这书已经绝版了,因为我自己最近重新回去读Hayek,而记忆中翻过的马老师这本书,是有原创贡献的,影响过我对哈耶克的看法。心心念念,就托人从国内带了一本来。晚上翻了一章,还是深受启发。当然我以前可能没发现,受美国学界简单直白的写作风格影响很久,发现马老师的文字就比较曲折反复。也可能是为了避免误解哈耶克的深意,所以马老师处理文字比较谨慎所致。
在PMRC开会的时候(PMRC2024参会杂记:旧雨依旧,新知飞扬),因为西雅图的温度骤降,就让承昕带了一件衣服过来,这次来DC开会,我又把衣服带回给承昕。我们现在合作的其中一篇文章拿到了RR,琢磨一下怎么修改。
CC让筱昀从国内带来差不多一箱小孩子的衣服回来,这是特别感激。毕竟现在飞一趟是真的不容易。跟筱昀一起聊了聊国内的情况,聊美国的大选,聊八卦。ARNOVA让人觉得愿意来开会,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也让你有一个回家的感觉。毕竟八卦这种事还是跟家里人聊起来最带劲。
在会场酒店和还在迷茫的好几位博士生聊了聊,主要是关于博士论文选题的事,我的意见还是之前说过的,一要有趣二要重要。(参见《如何做研究?从选题到发表》,《学界新手怎样选择研究主题》,以及《博士论文选题要选热点吗?比如AI治理或者应急管理什么的》)
我几年前还应马亮兄的邀请在人民大学做过的一个讲座《怎样写一篇对得起自己的博士论文》,我放在youtube上了
当然疑问就是:你谁啊我为什么要听你讲这个?可能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最后获得了PMRA的最佳博士论文奖,所以没准值得处在这个阶段的你听一下(按1.5~2倍速播放就好)。
2,
拿到tenure之后(从学生到学者:如何撰写申请终身教职(tenure)时的Research Statement 及其他),院长问我想做什么,我主要是想做两个方面的事。
第一是要完结之前开始的项目,尤其是自己心心念念要做的,以及合作项目;第二是准备更多做一些中国相关的研究,这有两个相互交叉的路径,但我可能会更倾向于以中国为例,而不单是去解决一个中国的问题。
在ARNOVA报告的第一个文章是我读博士二年级的时候的一个课程作业的升级版,属于第一个方面,就是要做完未完成的事情。这篇文章想探究对对政府的态度会不会影响个人的捐赠。当时因为我自己的见识和掌握的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的局限,自己也不是很满意,所以那个文章写完初稿之后,就一直搁置在那里。到了今年也算是见过世面了,突然想到这个文章可以用新的方法重新再做一遍。
我一直的观点就是数据不是最重要的,想法才是第一位。我们公开RICF数据大家可以免费使用,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如果你关心NGO和中国公民社会,就一定要看)。所以我比较佩服的是有一个新的想法,但是用了非常常见的数据和巧妙的方法,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章。这一次,我自己卷土重来做这个对政府态度和捐赠的研究,用了“枪”作为工具变量,以及匹配方法来确认因果关系。
3,
另外一篇文章和中国有关。这可能是一种代际的关系,现在从中国来的学生未必有我这样的中国情节,反正不做中国研究的也比比皆是。但我接下来想做的第二方面的事情,还是和中国有关,也和我为什么出来念博士是有关。
这个文章主要是讲不能忽视房间里的大象(参见《房间里的大象:社会组织党建与社会治理——读沈永东《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体等文章发出来了再说。
我主要想讲讲一个我自己的困惑。我上次去费城参加美国政治学年会APSA2024,也跟轶青聊了一会儿。叙旧聊些家常外,我们聊的最多的话题是到底怎么对待我们自己对中国忍不住的关心?你是研究中国问题呢,还是用中国作为证据来解一个理论问题?当然这两个其实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有时候甚至是重合的,但实际操作中却不那么容易把握。
中国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例如China Quarterly为顶刊),和以中国案例来推进对某一学科的研究,是不太一样的。从中国研究作为一个领域来说,那我自己之前几乎不做中国研究。尽管我们开源了RICF数据,但主要是为了推动非营利管理的研究(例如NVSQ,Voluntas,和NML为顶刊)。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区域研究里的中国研究,一般来说会要求你的研究去解决中国面临的一个具体的问题。比方说扶贫,那你有很多参与者,有政府有企业有非力组织有个人,他们如何行为或者说出台何种政策才能够达到更好在甘肃或者是在广西达到扶贫的目的?这一路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中国面临的问题。
另外一个路子是针对某一个学科的理论,用中国作为案例去验证,或者提出新的理论。比如发展(扶贫)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有,拉美国家有,东欧国家也有。具体来说,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积累人力资本。在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好教育,特别是女童的教育。因为通常而言,女性是受到结构性歧视的。那什么样的政策能够帮助提高女童升学率以及提高女童的学习成绩?这里面就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如说修建校舍,提供免费午餐,发放免费教科书,或者利用新的科技等,对我们PA来说,就需要知道哪一些政策是比较有效的。然后以中国某个地方为例,比如以浙江某地政府采用新的技术,来看是不是提高了女童的升学率以及成绩。
你当然可以说这不就是一个中国问题吗?但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去帮助浙江解决女童入学和提高成绩的问题,而主要是回答理论上技术能不能推动教育或者技术对发展的作用,只不过恰好用了浙江这个案例。
所以这两种不同的取向,一种是用中国的数据,去回答或者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种研究路径是利用中国的数据案例来回答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而这个理论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共通的,所谓理论无国界。
4,
我的困惑当然是到底要怎么结合或者怎么权衡。大部分从国内出来念人文社科的学生,可能和我一样有困惑:那就是要不要做中国研究。所谓家国情怀不管怎么样都会影响你。当然如李连江老师所言,先谋生再说,后谋道也行。这是很实用的建议。但长聘之后,要不要做中国相关的研究,要不要对中国的公共事件发声,以及更多介入一些中国的公共事务,是别人无法替你回答的问题。
之前在APSA上,我除了听实验方法,教育和民主之外,有空就去听China mini conference的报告,想知道大家都在研究什么。
然后看着一屋子做中国研究的成名成家的学者和跃跃欲试的新人,我羡慕他们的热情,但也担忧这屋子里的很多人找不到教职。这个领域真的有那么多职位吗?
我觉得大概能从DEI运动中学一些东西。那就是做大中国研究的市场,争取更多经费和职位。可能强调竞争性的思路是走不远。所以还是要回应有趣且重要的问题,而不是固守一个所谓中国研究的圈子。当然大部分政治学家的方法比我们在PA领域的更注重causal identification。但方法(参见《非营利研究方法谈》)还是要捡趁手的用,一篇文章如果没有回应一个重要且有趣的问题,就不会因为用了什么看起来新的厉害的方法就变成好文章。
我还是固执认为是道理决定文章的高度,而方法仅仅是方法而已。比如实验方法没有高下之分,往往是钱多钱少决定。
我其实在美国政治学年会上遇到很多熟人,这就意味着我的朋友圈里有很多政治学家 (参见《快乐社科联线》文字整理稿,长达3万多字,要收获需耐心)。我听说宾大的杨国斌老师要来,就想着要去见见。要感谢思瑶帮我临时注册招待会。不过杨老师一下嫩从人群中把我认出来,也是不容易:)杨老师和我算老交情了。那还是我在做【读品】,为The Power of Internet in China写书评的日子,那也还是对“围观改变中国”充满期待的日子。现在是一言难尽,能不能围观都得另说了。
另外就是在会场意外的碰到黄亚生老师,我原来以为他不会来参加美国政治训练会,然后我们就谈起我们一起主编的那本被禁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别人是《一出手就拿普利策奖》,我是一出手就成了*书作者。
5,
这次来DC开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季风书园。季风书园在DC重开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约了在ARNOVA和APPAM开会的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去季风参加《走线》纪录片的首映。
这让我想起我们在上海季风书园办的“今天,我们读书”的沙龙。也是在并不大的空间里,几十号人济济一堂,纯粹享受智性的快乐。(如果你有机会去DC,一定要去季风书园;如果你去了季风书园,请寻找“今天,我们读书”的彩蛋。)
也和季风书园的主人叙旧,聊近况,聊未来的发展。季风书园目前是打算注册成一个非营利组织,希望发展一切顺利。
开会这几天,DC天气不算好,下雨。季风吹旧雨,云影染深秋。
但以后去DC又多了一个必须要去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