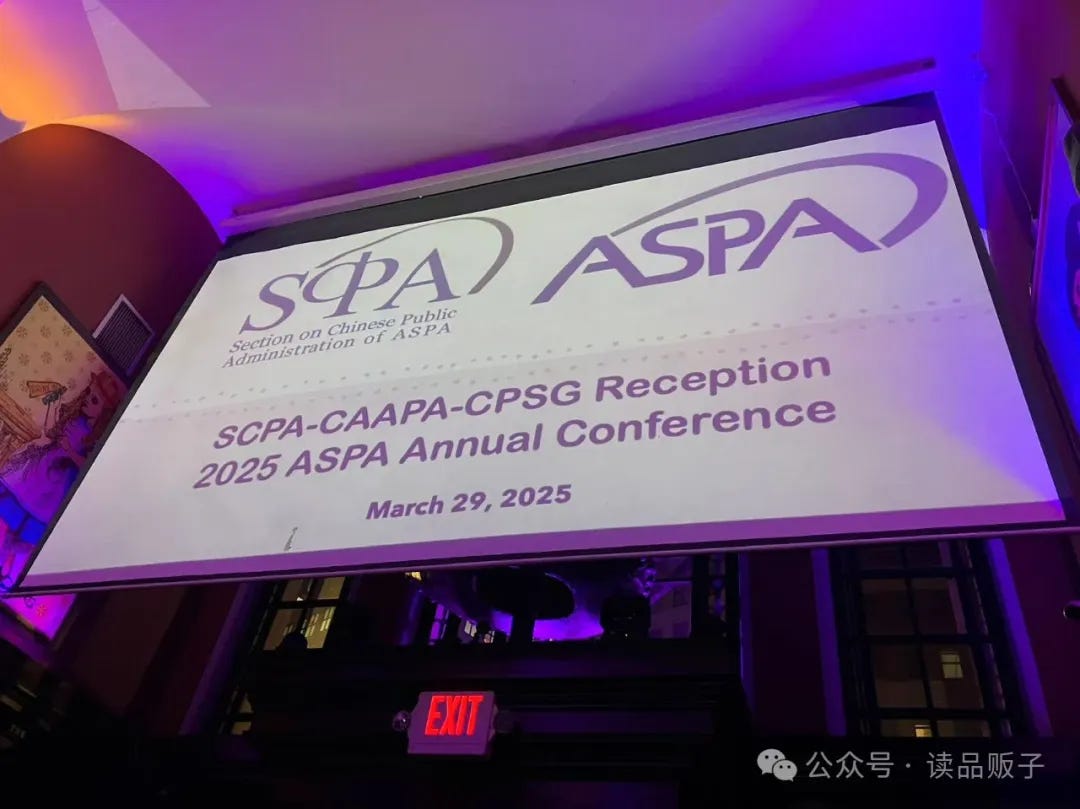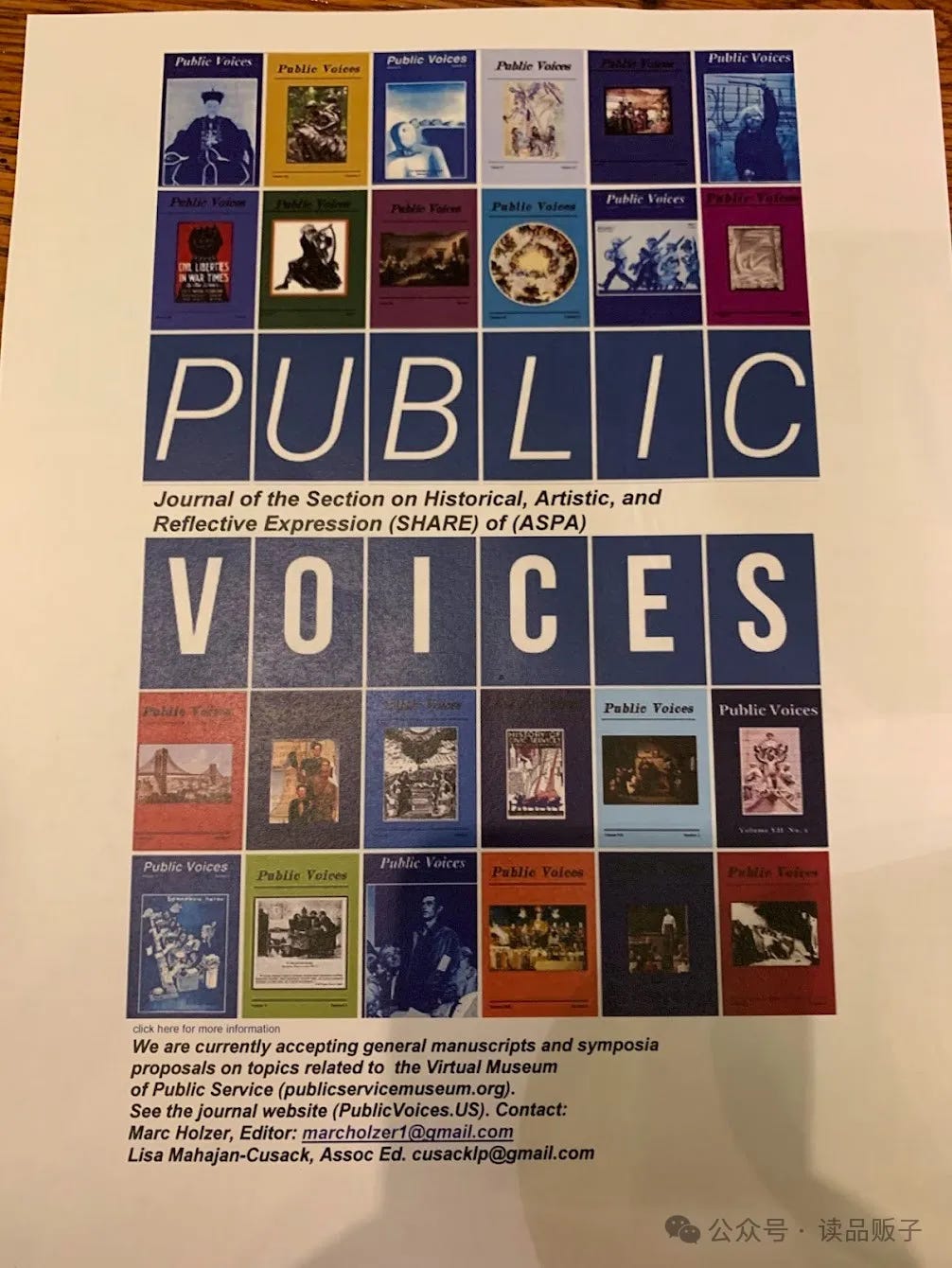ASPA2025参会杂记:这是个水会吗?
ASPA2025参会杂记:这是个水会吗?
李华芳 | 匹兹堡大学
樱花盛开的时节,去参加了ASPA2025年会,有几点感受和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ASPA是个水会吗?
因为ASPA还想着链接实践经验,这就造成了这个会议也有不少业界人士参加(主要还是学会需要考虑收入问题),不少师友反馈说这会上学不到什么东西。
尤其是一个panel有6篇报告的时候,甚至报告都得赶,更不用说展开讨论了。所以很水。我不反对这个说法。
但我在之前的《参会杂记》里说过,大会里的小会更重要。大会的好处是将平常不联系的人能聚集到一起,这样你再开小会就能和自己要合作联系的人聚一聚聊一聊。
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见一面多一次,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进展,也能增进感情,建立长期信任(参见程远《找工作的核心挑战:如何建立信任》)。人都是讲感情的,中外皆然。
所以是不是水会最终取决于你自己的预期。如果这个会有你想见的人,那它还是水会吗?
2,
今年非常高兴看到很多新面孔加入到PA研究的大家庭。而且很多人已经将“每会约见三五人”的建议落到了实处,因为我也被约了。
很开心的同时,要加一条因为国内外差异导致的评论。那就是国内的同学很客气(也可能是因为牛马惯了😂),和我们这些做老师的约吃饭或者喝咖啡,还准备付钱。这个是不对的。
至少在美国,尽管没有任何正式规定,但默认就是在你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哪怕你家里有矿,也该由老师付费。所以同学们约人也不要有心里负担。当你成为老师之后,pay it forward就好。
当然你成为老师后,也可以请自己的老师吃饭了。这次难得有机会,请Marc Holzer老师吃了早饭。Holzer老师退而不休,还在孜孜不倦的写书改文章,张罗Public Voice这个杂志,是活到老干到老的榜样。
Holzer老师对我们几代中国学生都是非常好的,虽然没直接给我上过课,但我从老院长身上学到的东西可就太多了(参见《记霍哲教授的三件小事》)。我现在特别喜欢和Holzer老师吃饭,因为我可以制止他吃第二根香肠,然后要求他把蔬菜吃掉。
3,
这次国内来的好多老师和同学,SCPA-CAAPA-CPSG的招待会估摸着快接近两百人了。我们的院长Carissa Slotterback也去了,主要是想和大家说,尽管中美关系瞬息万变,但有机会,希望大家多多交流合作。
国内的师友们在方法上已经迅速趋近美国的主流研究,甚至有超越的趋势。当然方法这种东西原本就不是难事,海归教师回去一代人就足够改变局面。(参见《非营利研究方法谈》)
为什么韩国的Soeul National University在PA领域厉害,甚至博士毕业生可以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就是因为faculty已经全球化了。当然人数上肯定是韩国教员为主,但教育背景上来说就是全球化了,教员绝大部分都是海外名校毕业。
再给一点时间,清北浙大等学校也做得到。我一直说一个学校的学术厉害是根本,学术上强了,其他资源会跟着来。
当然大家还是要更有自信一点。第一就是要意识到语言本身不是问题,哪怕你有口音,磕磕碰碰,也没事。老外如果用中文报告学术研究,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神奇?那反过来你用英文能报告学术研究,老外一样会觉得很神奇。
第二就是当老外违反规则的时候,是可以直接了当一些的。比如多占用了报告时间,可以直接打断。不然就对其他报告人不公平。更何况很多人讲得东西还没有你做得好。 所以在会议确定的规则内,大家可以自信展现一下自己的风采,不用迁就他们。
4,
我之前说过我在“研究中国的问题试图给出建议,还是以中国为例研究一个理论问题”中挣扎,无独有偶,我也发现这是很多学者共有的挣扎。(参见《2024ARNOVA参会杂记:中国问题,还是以中国解理论问题》)
理想情况当然是两者不冲突,解决理论问题的同时解决中国面临的困境。但现实往往就是中国面临的问题可能有很多不能一般化generalized的约束,导致一篇文章可能读起来过分中国化,离开了这个语境就很难成立,和其他文献对话。
如果要在理论贡献上有所作为,那么以中国为案例去解一个理论问题,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因为理论的延展性和覆盖面可能都要优于特定的区域研究(也会有很多人不同意,以你为准)。
李连江老师写过一篇《区域国别研究的两个取向》,我觉得说得很好。一是以理解中国为目的,二是以发展理论为目的而以中国为研究案例。
两者并无高下之分,只是不同取舍罢了。唯求在你认准的道上,不管不顾往前行。
(感谢刘鲁宁老师抓拍,献上四联表情丰富Style。主要是说我们的贡献一开始有这么大,然后慢慢变小,最后说你看,还是有贡献的。)
更多参会杂记: